英文原文:Uncomfortable User Experience
目前,电脑游戏、游乐设施、户外表演等文化体验的设计重点从传统的可用性目标,例如上手门槛、反应速度等,悄然发生转移,开始更多地关注像情感促进和审美参与等方面。这样的转移启发设计师利用非常规的方法,把传统的交互设计发挥到极致,具体的表现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强调歧义性,而不再是逻辑的清晰,或是把本来视为系统限制的东西反而转化为一场体验盛宴。这催生了有意为之的不适用户体验工程(discomfort engineering),以人体工学的方式创建出激烈的、具备令人难忘的互动性和挑战性的主题。
不适用户体验工程需要回答五个主要问题:令人不适的互动潜在好处在哪里?这种互动可以采取怎样的形式?如何产生不适感?怎样将不适感嵌入体验?最后,有哪些必须解决的伦理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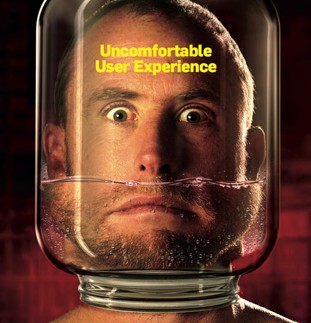
令人不适的互动会导致用户一定程度的痛苦。通过用户精神上的无助、恐惧、焦虑,或是人身的移动、劳累和痛楚来实现。虽然痛苦并不能说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最终目标,但不适感却往往可以通过这么一种过渡的方式来实现三个主要优点。
1. 娱乐性:游乐园的游乐设施采用极端加速、突然下降、头脚倒置等来刺激感官,创造少有的快感,而游戏和电影中,预期的危险则通过悬念来产生不适感。恰到好处的不适感可以增加主观上对于体验的强度和记忆,提高参与者的流动感,让人们感觉身临其境,或是产生电脑游戏情节相关的深度焦躁的心理状态。
2. 启示性:不适感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挑起我们对于感受和反应的反思。具有挑战性的主题的艺术作品,可以采用建立一个恰当的语境,要求个人的承诺、避免庸俗化,促进对于不适体验的同情和尊重。
3. 社会性:不适感可以通过所谓的“共享通道”,提示社会纽带的存在。比如一群小朋友“第一次”一起坐过山车,或是青春期的男生一起看一场恐怖电影等,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于在团队建设活动中加入对体力要求很高的任务。
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领域,创造不适感其实有着悠久传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诗人和剧作家 Bertold Brecht 宣布将在剧院中引入一定程度的异化(verfremdung),即造成不安或不适感鼓励观众“从另一个角度欣赏”。20 世纪后期则更是不断地突破边界,如 1974 年 Marina Abramovíc导演的“O节奏”,观众被邀请使用枪、子弹、折叠刀、斧头等,与演员的身体互动。1971 年,Vito Acconci 的“17 号码头项目”中,观众被邀请参加一个深夜的会议,到一个废弃的码头听 Acconci 坦承一个秘密。如果说艺术家都比较疯狂的话,不适感其实也早已被主流娱乐采用,游乐场会提供电脑游戏让人们体验感官的惊险和恐慌,甚至还有电击游戏控制器出售。人体工学研究员以及有形接口设计师也会尝试不适感,例如 2007 年发明“肉体手册”装置中,系统会直接通过操纵用户肉体与之互动,产生劳累、紧张或压力的物理作用(场景包括如拳打脚踢和吊在酒吧天花板上等);“从皮肤上寻求神经感应”系统,要求用户提高步进速度以听到一段疯狂的朋克诗;“中介肉体”逾越传统的社会规范,通过要求参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敲打中风演员的身体,探求一种交互式的音域。
人体工学主要用四种方式建立不适感。
通过五步将不适感嵌入体验。不适感不是我们的整体目标,而是一个过渡旅程。
1. 阐述:建立体验的初始框架,设置适当的期望。
2. 上升:在体验中增加不适感。开始预测和悬念构建,例如,过山车从逐渐上升的斜坡滑向第一个速降。
3. 高潮:预测变成了实际体验。有两个重要的原则指导设计的这一刻:首先,它必须是暂时的,达到迅速传递的效果。
4. 下降:释放或宣泄的时刻,虽然不适但是伴有强烈的快感,甚至兴奋的感觉。设计人员可能会寻求将这样的感受适当延长一段时间。
5. 收尾:最后一幕,强调反思的重要性,让参与者吸收不适,通过讲故事与他人分享,提供新的见解,或者干脆享受幸存下来吹牛的权利,可以用拍照或发放纪念品的形式实现。
必须解决伦理挑战。第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不适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体验设计师蓄意产生不适感,就需要评估行动的良性及其后果。这要通过娱乐性、启发性和社会性来说明。参与者能收获什么长远利益?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师可能会问:参与者知道在事后会发生了什么,才会仍然选择参与?个人的选择权也很重要。用户有权刻意选择不适感,但特别要限制其对他人的影响。要否签署知情同意书,是具有挑战性的文化体验,尤其是那些涉及惊喜的互动——顾名思义,参加者不一定事先知道。撤回权:这有时并不现实,比如上了过山车就下不来了,虽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用户在任何一点应该都知道自己有没有回头路。隐私和匿名就不用说了。最后,需要管理风险,这要求在施工或心理设计上多留心眼。